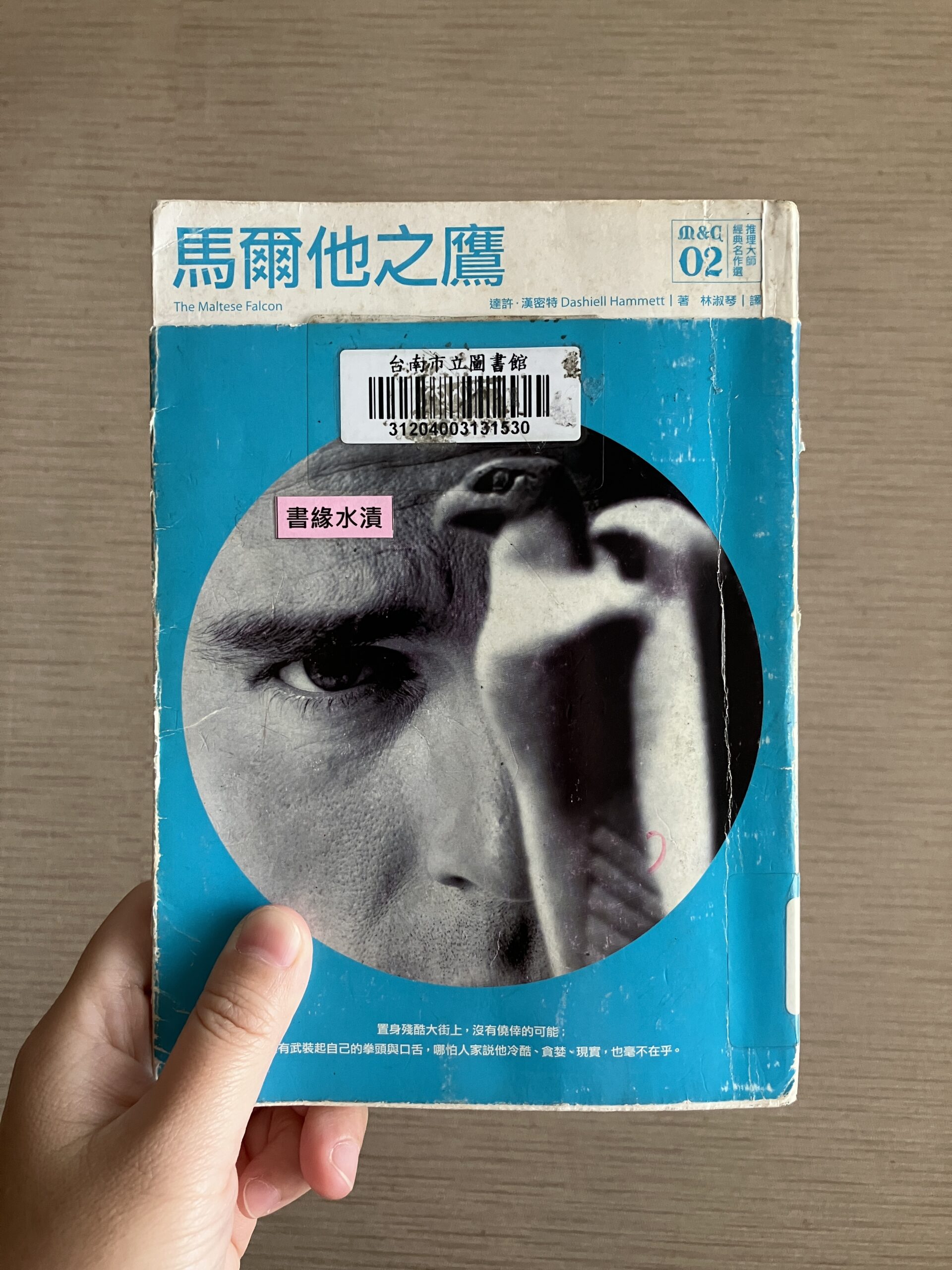
《馬爾他之鷹》(The Maltese Falcon)的故事,始自一樁看似尋常卻又疑點重重的委託。一名自稱萬得麗小姐的神祕女子走進了山姆・史貝德與邁爾斯・亞傑合夥經營的偵探社,請求他們跟蹤一名男子。交涉過程中,萬得麗小姐緊張發抖,面對史貝德與亞傑的交換眼神與輕薄打量(亞傑甚至背地裡吹起了無聲口哨),可以說萬得麗顯得坐立難安,甚至有些脆弱。然而,柔弱姿態與伴隨的不安氣氛,不過是將眾人捲入漩渦的誘餌。
亞傑在執行任務當晚遭到殺害,跟監案驟然變調,史貝德失去搭檔,更立刻成為警方的頭號嫌疑犯,因為他與亞傑妻子愛娃的私情早已不是祕密。為了洗清嫌疑,也為了探究真相,史貝德周旋於萬得麗(真名為布里姬・歐香奈西)、黑幫首腦賈曼,以及地中海人開羅之間,還時不時要應付視他為眼中釘的警察丹第隊長。眾人爾虞我詐,全為了爭奪那尊價值連城卻行蹤成謎的「馬爾他之鷹」。
小說甫一開篇,達許・漢密特(Dashiell Hammett)便藉由對主角史貝德的描述,定下了故事基調。這種幾乎完全以外部視角勾勒角色的手法,是冷硬派敘事的經典特徵,角色的真實感受與企圖多被隱匿。讀者與主角一樣,對眼前的謎團所知不多,我們只能憑藉角色們交手的姿態、對話與採取的行動來進行推敲。
因此,第一個章節「史貝德與亞傑」的設計顯得格外重要。漢密特花了一些篇幅描繪史貝德的外貌,以及眾人在偵探社內部空間裡的對手戲,那些觀察不純然是肖像速寫,而是為了賦予角色更深層的性格內涵。
對於史貝德外貌的勾勒,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那奇特的「V字」幾何結構,從嘴、下巴與人中,到最後收攏於鷹鉤鼻尖,一切都呈現出尖銳收縮的方向性。這種猛禽似的外觀,帶著精確、犀利的視覺暗示,確立了史貝德善於盤算且目標明確的本能。
與此同時,漢密特又矛盾地稱他為「金髮的撒旦」。直覺上,金髮男子在西方設定中常與純潔或英雄連結,而「撒旦」之說,則將之推向道德的灰色地帶。也就是說,表面順眼的輪廓,卻不會拒絕靠近罪惡與誘惑,不難想見他習於遊走事理邊緣的彈性認知。
史貝德的身形,則是在他接待萬得麗時透過對比所呈現。他那又寬又厚的圓錐狀身體與粗實的大手,對照萬得麗無稜角的細手與修長肢體,立即確立了史貝德作為空間的主人與力量的主導者。然而,這具強悍的肉身也帶有他「金髮撒旦」的缺陷,諸如罪惡與誘惑的傾向,或對萬得麗這個人(及她的皮夾)進行的輕浮盤算,恰恰滲透進了這個本該理性的偵探領地。
隨著故事開展,我們不僅無法窺進史貝德的內心,女主角歐香奈西更是一個難解的謎題。她以假身份現身,而從劇情推進與偶爾述及過往的片段訊息中,我們看見了偽裝與連篇謊言,以及典型「蛇蠍美人」所運用的美色之利。
雖然有一種文學批評觀點,傾向將這種角色的空洞視為功能化的解釋,認為她僅是男性作家投射「致命誘惑」的刻板想像,反映了那個時代對女性地位崛起的焦慮。然而,若要理解這部小說的張力,我們不能僅將她視為無數面具拼湊而成的單薄平面,而應將她視為史貝德必須面對的「混亂」化身。這道謎題是對史貝德生存哲學的終極測試。

隨著亞傑與德士比(原本跟蹤的對象)相繼死於非命,史貝德被迫走入險境。他需要歐香奈西作為線索來接觸背後的勢力,更需要確鑿的證據來將真兇繩之以法,否則身陷囹圄的就會是他自己。這使得史貝德與歐香奈西的關係,演變成一場刀尖上的雙人舞。謊言與真實交織,情感與計算糾纏。史貝德必須讓自己看似陷入情網,才能引蛇出洞,然而「當你凝視深淵,深淵也凝視著你」,投身謊言,也面臨被黑暗吞噬的風險。
支撐史貝德在深淵中不致迷失、並能貫徹冷酷行徑的,並非傳統正義感,而是他獨特的道德準則與世界觀。史貝德曾看似漫不經心地對歐香奈西講了一個故事:一個人好端端走在路上,卻差點被建築工地的橫樑砸死,從此拋家棄子去過新生活。或許可以將之視為解開解開史貝德內心的鑰匙。我手持的譯本將人名翻作「石藝」(Flitcraft),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的《神諭之夜》也有引述這個段落。
這個世界的本質是隨機且荒謬的,死亡隨時可能降臨。歐香奈西(或她代表的一切)就是那根隨時會掉下來的橫樑,那樣的時刻,是窺見生命所藏有的祕密,千鈞一髮的瞬間;也是領悟不可控的機運與隨時可能與毀滅擦身而過的觳觫,包括無法憑恃的、飄忽不定的情感關係。史貝德只能緊抓著自己的一套「行規」:當合夥人被殺,你就必須做點什麼。這無關乎喜好,而是為了維護私家偵探在這個險惡行業中的生存尊嚴與鎮懾人心的能耐。行規就是指南針,是籠罩大霧的世界,他唯一能掌握的秩序。
在此,史貝德心中的天秤已然浮現。天秤的一端,歐香奈西試圖拋出的最後籌碼是愛的呼喚,然而這一端是史貝德所窮舉的各種現實後果,「我們擁有的只不過是也許你愛我也許我愛你而已。」對史貝德來說,這愛的邏輯與那尊引逗眾人慾望的寶物如此相似。
最終,那尊眾人搶奪的馬爾他之鷹,剝除偽裝後,只是一塊毫無價值的塗漆鉛塊。小說中關於找個「代罪羔羊」的段落極具諷刺意味。黑幫首腦賈曼對殺手小子威馬似乎情同父子,卻能帶著慈祥的微笑準備犧牲威馬,他說道,如果失去兒子,固然會感到遺憾,不過兒子能再有,「但是世上只有一隻馬爾他之鷹」。

這正是慾望本質的揭露,眾人被貪欲驅動的追索,實際是對幻影的徒勞追逐。歐香奈西所獻上的愛情,外表是聖杯般無價的承諾,內裡卻是裹著層層謊言與操縱,揭穿了,終歸是沉重且無用的鉛塊。
史貝德看穿了歐香奈西的謊言,也看見了寶藏的空洞。他深知,如果因為愛而放過殺害合夥人的兇手,他並不會得到救贖,只會讓自己淪為隨時可能被出賣的傻瓜。那不是愛,那是混亂本身。因此,史貝德過分清楚地權衡之後,咬緊牙關說出:「我不會為你當傻瓜。」
但他贏了嗎?
小說的尾聲,史貝德回到了偵探社。那裡沒有英雄凱旋的榮耀,只有早在門外等候糾纏的愛娃。這是一個迴圈,彷彿呼應了寓言的後半部:石藝離家多年後,在另一個城市生活,與原本一模一樣,但他並沒有自覺。
事件解決了,這樣略顯狼藉的名聲或許甚至有助於偵探的事業。只是,史貝德雖然拒絕成為感情的傻瓜,似乎也無法逃脫命運的重力,他在這個隨機而荒謬的世界裡繞了一大圈,堅守了原則,卻兩手空空地回到了原點,回歸原本那個充滿道德瑕疵與瑣碎糾纏的舊秩序裡。不過,他的自覺或許就是最寂寞也最動人之處,生之荒謬終究是無法戰勝的,生存意味著清醒地看著自己繼續孤獨的旅程。
作者/傅淑萍
現為「我們的教學事業有限公司」講師,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部落格「樂遊原」與IG「樂遊原(@leyou_yuan)」共同經營者。曾任聯合報文學寫作營講師。曾擔任聯合盃作文大賽閱卷與命題老師。
本文章來自《桃園電子報》。原文:副刊/冷硬派偵探的行規:達許・漢密特的經典作品《馬爾他之鷹》







